代际自觉下的批评突破——评李徽昭《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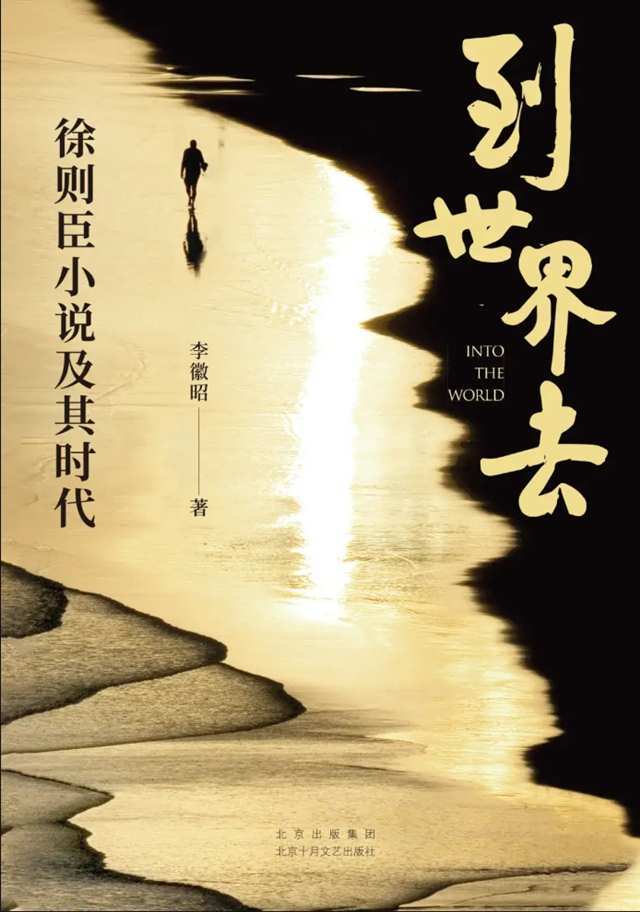
编前语
近日,根据作家徐则臣茅盾文学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引发广泛讨论。该剧聚焦大运河畔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与奋斗,虽对原著历史纵深感有所取舍,却以青春叙事激活了运河文化的当代意义。徐则臣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到世界去”的精神内核,他笔下的个体与时代共振,既有对远方的渴望,亦有对根脉的回望。扬州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李徽昭所著《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深入剖析了这一主题,揭示其如何通过文学地理的构建,勾连历史与现实,映照一代人的精神迁徙。此番改编热潮,恰为重新审视徐则臣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日常中,虽然李徽昭与徐则臣深交多年,为这本《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到世界去》)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但作为批评家时,李徽昭又刻意注重身份立场转换,与徐则臣保持距离及严肃理性,并对徐则臣的创作呈平视姿态。于是,《到世界去》的正文和附录便是作为批评家的李徽昭和作为徐则臣朋友的李徽昭的最真实两面。
在《到世界去》中,李徽昭亲切地称“我们这代人”,显然是将自己与徐则臣置于同一时代语境下,展现出一种自觉的代际视角。
70后大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裂缝中,由此建构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精神立场。同为70后,李徽昭与徐则臣出生、成长于苏北农村,都有着学院派的学习经历、相近的工作经历,以及相似的海外体验。这一时代裂隙中的时代经验与文化背景,使作者更能以70后的同辈视角探究徐则臣小说中的世界化书写。尤其是,时代裂隙恰恰与全球化时代相吻合,这样的亲历,使得作者择取了“到世界去”这样的徐则臣观测视点。
如何通过徐则臣小说观测其与时代、世界的联系,这是《到世界去》的核心议题,作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尽解释。如徐则臣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归国人物形象、京漂的乡土尴尬处境,以及体现世界性的食物交通等“物”的书写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徐则臣在“京漂”系列小说中乡土隐退的迷茫这一章时,作者在结尾附录中通过几十年前有关乡土的小随笔和手记,表达了类似的焦虑,这何尝不是70后一代人的精神共鸣?正如书中所说:“70后作家所遭遇的便是一个‘无土时代’”,出身于乡土,又恰逢现代化的发展,于是注定远离乡土。徐则臣家后的河被填平,李徽昭农村的家被拆迁改为工业园区,这是他们共同的模糊的乡土处境。乡土依恋的被迫消亡又何尝不是“到世界去”的另一层推力?因此时代的面影正是通过细化到70后的个人生命体验中,从而使得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后必然要“到世界去”并与之发生联系。
在梳理徐则臣小说创作时,作者还特别注意比较视野,关注徐则臣作为70后的横向对比、纵向转变以及在文学史坐标轴中的定位。横向上,作者发现70后作家多聚焦于个体成长经验的书写,“历史的阙如”使得缺少文学深度与思想厚度成为70后一直被诟病的点。然而,徐则臣却能从中脱颖而出。作者不失偏颇地指出徐则臣早期《夜火车》《水边书》等的创作是起步于生活经验,但《北上》则是徐则臣以历史书写走出直接生活经验、挑战自我的开始,这也正是徐则臣没有止步于“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被视为70后佼佼者的关键所在。在纵向转变方面,作者指出徐则臣的创作经历了从悲观的理想主义到积极的理想主义的转变。早期“花街”系列作品常以留白结局,带给读者无尽的遗憾与期待;而《北上》则以理想主义的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徐则臣创作由消极的理想主义到积极的理想主义的演变。
但作者的研究并未仅仅关注徐则臣,而是将徐则臣与50、60后等前辈作家进行对比,探讨其创作在传承与突破中的独特性,以及与世界话语的接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呼应。比如,作者深入剖析了徐则臣小说中,如现代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交通、美食、人物等“意象”塑造背后的世界话语。在文学史视域下,将徐则臣的小说与前辈作家、同辈作家的创作进行文化呼应,再与新写实、新历史、先锋小说的区分并联系,从而使徐则臣的创作呈现出与文学史对话的独特魅力。在古典意象如“船”的营造上,不仅承续了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古典诗意美学,还通过花街人的挣扎,展现了在传统和现代碰撞下的“最后一个”的无奈。在底层人物的展现上,作者以温情的目光,以自己的乡土经历和情感俯下身去体察他们。食物书写上,作者注意到徐则臣小说中“不同种类、人物、情节与不同食物形成内在的文化同构”现象,“与莫言、余华等前辈作家形成了文化映照”。作者还捕捉到《北上》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关系,《北上》的历史感、极尽细节之能事的描写以及多声部的先锋形式,正是在新历史、新写实和先锋小说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更别致的是,在《到世界去》中,电邮、随笔、照片、公报等异质文本的介入,为文学批评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作者突破了传统批评“就文论文”的单一范式,在每章节结尾都附上一些随笔、电邮以及相关政策新闻等实证材料。感性的小随笔和真实且亲切的古早邮电往来的融入,打破传统评论过于理性客观以至略显生硬的范式,这不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更是与正文论述紧密呼应的匠心安排。比如第一章“中国与世界”,作者在正文详细地阐述了徐则臣参与国际活动获取世界经验,从而对世界性进行表意后,在该章节附录处,也附上了其在美国访学时的随笔,以个人世界经验与之相呼应。另一方面,相关实证材料的插入显示出作者作为学者和评论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在第四章论述徐则臣“京漂”小说乡土退隐时,也贴切地附上了自己的回乡手记。最后一章,作者以与徐则臣纯访谈的形式,让读者与徐则臣面对面,直观感受徐则臣的内心世界,突破了传统评论仅通过作者口述感知作家及其创作的局限。这种评论文体的创新不仅是作者对于评论文体的突破,更是文学评论人文关怀的践行。
总体而言,这本《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通过对徐则臣的系统考察,以此延伸出对代际、对民族立场的世界话语的理性分析,并主动实现批评文体的创新,使理性研究与感性体悟之间实现了完美平衡。
 公安备案号 50011202501662
公安备案号 50011202501662